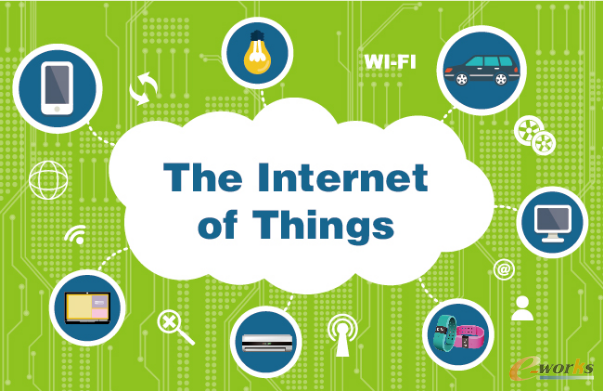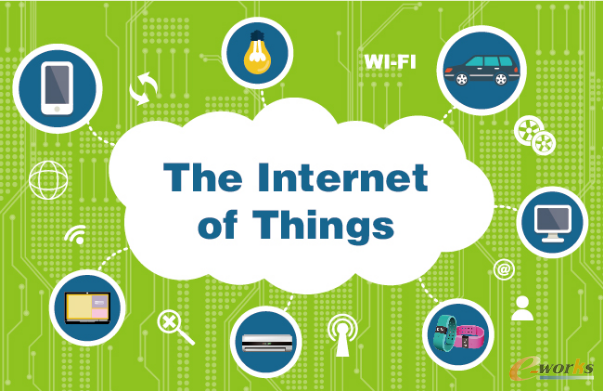虛擬化特別是自身的虛擬化是“
云計算”和“大數據”的基礎。“虛擬化技術”基于算法(計算機)自身的虛擬化,“云計算”則建立在互聯網本身的虛擬化過程的基礎上;“大數據”則從真實到虛擬相反的方向,從對虛擬化了的巨量數字信息中回到現實中的真實。“云”是一個文化概念,“云”以“云計算”和“大數據”等多層交互實現了知識和信息世界的再整合,今天在物質、信息、知識和人的認知上的文化再整合代表了一種新文明。“云”在工具理性意義上的不確定性最終表現為人性的自由。
在IT領域與商業領域的交集中,幾乎在短短的幾年的時間里,“云”、“云計算”(Cloud Computing)與“大數據”(Big Data)等概念如日初升,戴著“創新”這頂桂冠,已經成為席卷全球的洪流,并正在迅速地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最富創造性和嗅覺的精英幾乎都為之狂熱。“云”已經是現實,但是我們仍然沒有這個概念的精確定義,“云”的能量和影響之大似乎難以預測。“云”這個概念目前尚定位于“云計算”這個二級概念,“云”只是模糊地被理解為互聯網龐大結構體系中正在被再開發的不可估量價值。在IT領域,“云”只被狹義化為“云計算”,在商業領域,“云”似乎就是“大數據”的代名詞,但真正的大數據卻是數據專家和程序員們望而生畏的苦海,這一切都令人即興奮而迷感,“云”即是明喻,又是隱喻,所以這些相關名詞和對它們的不同的解釋大體都是“盲人摸象”,常常更令人糊涂,無法把所有這些極為豐富的概念內涵整合起來,只有把“云”理解為文化的本質,才能看到他們的時代特征、普遍性和歷史性的意義。
“文化”一直是一個內涵豐富但沒有公認定義的概念,“文化”的抽象性無法從這個概念無所不在的普遍性中去定義。在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的視域中,“文化”就是“文化的整合”,只有從這個高度才能理解這個現代“云”:“云”就是現代文明的新整合,“云計算”和“大數據”作為工具理性,在現實和虛擬之間進行創造與融合,“云”是它們的整合性本質,這個本質使其成為現代歷史中的一個里程牌。
“云”已經成為了現代新文明的特征,如果你沒有接觸到它們,就不算是最“現代”的現代人,而如果你沒有意識到這點,就算不上是現代的“文化人”。
一、“云計算”——從真實到虛擬
由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支持的“虛擬世界”,可以看作是現代人類所面臨的種新文明。和以前所有時代中的神話世界、宗教世界、藝術浪漫、虛幻世界、精神理想、烏托邦等等不同,基于物理技術的“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是有實時性關聯的,因此與超越個人的先驗性、超越集體的抽象性、超越理性的純粹性不同,“虛擬世界”只是空間意義上的虛幻,它的背后有算法實時性(Actual Time)的時間性本質。
“virtual”這個英文詞既是“虛的”,又有“有效的”含義,比如virtual president,就是“事實上的主席”的意義;中文“虛擬”就可以理解為對現實的模仿,“虛擬世界”就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形式化重構。
虛擬化技術是理解“云計算”這個概念內涵的基礎。與一般意義的計算機仿真技術不同,虛擬化技術是對計算機和計算機體系(泛計算機)和互聯網在自身中對自己的仿真,就是說,雖然在形式上具有“虛”的性質,但在時間性上是一致的,因此,虛擬世界和現實具有實時性(actual time)關聯,這種實時性正是“算法”的內涵性本質。
虛擬技術是基于計算機程序嵌套功能的高級程序技術,虛擬技術最初成功的例子是“虛擬機”(Virtual Machine),即在一臺具體計算機的操作系統中仿真出虛擬計算機,這臺虛擬機能夠像真實機器一樣在這臺物理機器中被操作、運行。
在互聯網時代,這種復雜的程序內嵌技術,由虛擬機擴展為對網絡體系的仿真,這不是指在一臺物理機(數據中心或超級計算機中的情況特別對待)中對網絡進行仿真,而是在網絡中對網絡本身的虛擬化,這才是現在所說的“虛擬化技術”的本質。
“虛擬化技術”基于網絡的本質——互聯網整合,本質地說,互聯網就是通過虛擬化技術實現的“互聯整合”。在具體的機器之間進行信號傳送并不就是網絡,網絡形成的關鍵在于將物理機器虛擬化,就是將一臺具體的物理機器與一個基于網絡拓撲的地址對應,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虛擬化的IP地址,比如我們向某人發一封電子郵件,并不需要寫上收件人的物理地址,電子郵箱地址就是收件人的虛擬地址,通過這個虛擬地址最終能達到某一臺物理機器,這是因為這個虛擬地址與傳輸過程中的網絡設備(各種線路、交換機、路由器、終端等)有動態的綁定的關系,使一封信件能自動通過這種動態的傳輸路徑達到最終目的,就是說,以前的互聯網,虛擬地址與網絡的實際物理聯接(術語:網絡拓撲)在整體上是綁定的(術語:網絡設備控制層與數據流合并運行),我們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互聯網是通過虛擬地址化而整合的一個“真實”的網絡。所以,互聯網即是虛擬的,又是真實的,這種自身的互補存在性是所有基于虛擬技術的現實世界的新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稱之為一種新文明的標志。
互聯網本身的虛擬化,就是在物理機器地址已經虛擬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將網絡的物理連接過程虛擬化,這就將網絡的所的物理體系和物理過程虛擬化了,就像計算機中的芯片一樣,硬件與軟件分離,網絡物理拓撲體系成為了類似芯片的集成硬件,而“云計算”就可類比于計算機中的虛擬機軟件一樣,是在這個網絡拓撲體系運行過程中虛擬化運行。
由于硬件和軟件是可以一定程度相互替代的,這個虛擬化的“網絡硬件”與“云計算”正處在相互分化形成時期,當前成為了非常火熱的兩個密切相關的技術:SDN和NFV。
軟件定義網絡(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 )就是一種虛擬化網絡和運行架構,SDN的核心理念是通過對物理網絡結構的虛擬化而實現對網絡的集中控制,即網絡中的虛擬網絡構成技術,SDN可類比為虛擬化的“網絡操作系統”。SDN的做法是將以前的網絡控制層與數據轉發層的綁定關系進行分離,在控制層和轉發層之間提供標準接口,通過網絡軟件來控制這些虛擬化的設備的工作,最終實現編程化控制底層硬件,從而控制整個網絡拓撲,實現對“數據流”動態化控制的靈活性和優化調配。因此SDN技術簡要地可歸結為“控制和轉發分離”、“設備資源虛擬化”和“通用硬件及軟件可編程”。
如果說SDN類比網絡體系的虛擬芯片,網絡功能虛擬化(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NFV)就是運行在這個虛擬芯片中的“軟件”,當然它也可以就是虛擬網絡自身的操作系統,如“云管理技術”配置網絡服務虛擬設備,服務器虛擬化托管網絡服務虛擬設備,通過操控“服務”本身實現網絡功能虛擬化;NVF也可以是網絡運行的應用軟件,比如對網絡流量轉發進行編程控制,實現網絡無縫轉發服務等等。因此,SDN可以看作是最基本的“云計算”。SDN和NFV是相互結合的,NFV可以通過操控SDN來編排設備的連接,實現對網絡基礎設施的最優化控制,這些超越層次的虛擬化能力正是“云”整合的本質。由此可以看出,層次化的虛擬化是“云計算”的關鍵技術。在更深的意義上說,虛擬化就是“云”的抽象性本質的實現,但是目前,“云”這個基于層次化的“虛擬”的意義的內涵遠沒有得到注意。
目前,“云”這個概念只是外延地理解為“云計算”,以“云計算”來定義的這個“云”,只是指互聯網上的大量的服務器集群、網絡設備資源、數據中心等具有的潛在可開發價值,包括所有的硬件資源(以CPU為最底層的服務器、存儲器)和軟件資源(如操作系統、應用軟件、集成開發環境等),目前這個“云計算”的定義就是從廠商角度出發,把所有的資源“云”化,這樣,本地計算機只是聯接“云”的一個“端點”,遠端的“云”為你提供需要的強大的計算能力和數據。這種有些含混的“云計算”的內容大體由分布式計算(Distributed Computing)、并行處理(Parallel Computing)、網格計算(Grid Computing)構成,而且相應定義的“云”也有二個二級定義,狹義的就是指廠商自己通過虛擬化技術,組成數據中心或超級計算機向客戶提供計算、存儲、虛擬網絡等服務——即自己先“云”化成佛再渡人的“云—端”模式;廣義的“云計算”指廠商向客戶直接提供所有層次“云計算”服務,從個人來說,最終可以實現個人的“云”化。
從廠商的角度上看,根據引用得最多的NIST(美國商務部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所)的定義,云計算有SaaS、PaaS和IaaS三大服務模式。
1.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軟件即服務):運營商提供的軟件應用服務,SaaS提供完整的可直接使用的應用程序軟件,如CRM(客戶關系管理)、HRM(人力資源管理)、SCM(供應鏈)以及
ERP等企業管理軟件。傳統的瀏覽器可以看作是面對個人的“云計算”。
2.PaaS(Platform-as-a-Service平臺即服務):把服務器平臺或者研發的平臺作為服務提供。
3.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礎設施即服務):提供數據中心、基礎架構硬件和軟件資源,如服務器、操作系統、磁盤存儲、數據庫、信息資源。比如通過 Internet管理企業資源,IaaS分為兩種用法:開放的“公共云”和內部性質的“私有云”。
實際上,“云計算”的外延正在飛快地擴展,因此不能從些概念的外延中得到它的真正定義,“云計算”實際是從不斷地虛擬化中得到不可估量價值的數字化工具,因為“云計算”的本質源自于工具理性,“云計算”的最終內涵是算法,在算法的計算機化之后,虛擬化技術使經典意義的算法再次插上了騰飛的翅膀。從現代新文明的高度去闡釋更高的概念“云”與基于算法本質的“云計算”的在系是一個深遠的視界。
二、大數據——從虛擬到現實
“大數據”是由計算機算法和互聯網的虛擬化枝術在機會嗅覺最敏感的商業領域引發的,這是一種超越常規的文化整合現象,知識分科和社會分工此前一直是在不斷的分化和分離的方向上進行的,虛擬化技術似乎使傳統世界分裂為二,但大數據卻從相反的方向,從對真實的數字化虛擬中回到另一種現實中的真實。虛擬化就是“符號化”、“數字化”、“量化”,數字“信息”就是一種量化的“存在”,大數據建立在這種“數字云”之中,但大數據不是數據本身,而是對大數據的處理和提取的能力,因此大數據是“知識就是力量”的一個現代版本,從商業角度看,數據就是金錢,財富似乎唾手可取,這種量、速度和多樣化結合形成的新價值很快地在醫療衛生、金融、交通、物理網絡、城市、媒體、社交、社會秩序、政治情緒以及整個社會領域,掀起了難以想象應用甚至是風暴。
業界現在公認“大數據”的特征或價值為4個“V”(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樣、Veracity真實),但這只是“大數據”這個概念的外延,“大數據”的特征在于數量、速度、多樣性的同時性爆發,構成了人們面對的似乎是一個不同的世界,一個隱藏在數量巨大的瑣碎平凡生活中的“云”世界,一個完全是信息風暴呼嘯的能量世界。
人類的自覺“表達”是人與動物的區別之一,人類日常生活中所謂“價值密度低”的點點滴滴信息一直只是歷史中的塵土,只有如年鑒學派等才會以特別的歷史性眼光注意到,傳統的世界觀:統一性——可控制性、因果性——可預測性、經驗——可靠性等,基本上是建立在大事件或可靠的統計數據研究上,從來沒有將這些數量巨大的數據灰塵當作有價值的信息處理,“大數據”把日常生活所有的信息虛擬化了,“大數據”是數字、符號、語言、圖像等表達內容的數據化的整合,“大數據”在傳統認知中注入了完全陌生的因素,改變了人的世界觀,同時也以時日更新的速度改變著最普遍的日常生活,這種巨大的普及性力量史無前例,成為了“現代”中的一代新文明。
“大數據”與“云計算”具有工具理性的共同本質,“云計算”與“大數據”的結合,似乎將傳統的工具理性推向了極致,但也可能是工具理性最后的邊緣——“我們不再需要理論了,只要關注數據就足夠了”!這種相互作用甚至隱藏著“歷史的終結”的狂妄,給“未來可以預測”、“機器可以超越人的智能”這樣野心以最強烈的希望,使理性的人類直接感觸到對文明本身的疑慮,但無論如何,它們只是“云”的二級概念,只有真正地理解作為“云”的文化。我們才有可能消解文明進步中的不確定性。
三、“云”——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確定性幾乎就是工具理性的代名詞,一直是科學和數學的驕傲,但一個陰影始終籠罩著這一切,解決某些問題時所要求的計算能力在這個問題的展開過程中呈指數性地增長,超過能行算法的計算能力,面對這種問題與工具之間的能力比較,我們能否得到一般性判斷?這實際就是學術界著名的P vs. NP。
我們今天仿佛是突然被數字信息洪流所裹脅,被“知識爆炸”所壓迫,我們直接面對的困惑是:這種巨大數量級(1Nonabyte=1024BB,1 Brontobyte=1024YB,1Yottabyte = 1024 ZB,1Zettabyte=1024EB,1Exabytes=1024PB,1Petabyte=1024TB,1TeraB=1024GB,1GigaByte=1024 MB)的本質是什么,它們到底是確定性的還是不確定性的?
在算法理論中,確定性(P)與不確這性(NP)的關系于直是一個似乎清楚但實質糊涂傳統問題,不確定性問題是工具理性的確定性的對立面,算法理論一直在對不確定性事物的確定性追求中,但卻很容易丟失這些問題的不確定性的本質,這已經困擾著這個領域的學者大半個世紀,對于本質的不確定性問題,算法工作者竭盡全力也只能得到最優近似的答案,但“大數據”和“云計算”與這種傳統形勢不同,對真實的虛擬和逆虛擬的真實似乎改變了“確定性”和“不確定性”之間傳統的關系,它們把工具理性從單純的工具方法導入到工具理性本身的虛擬化和虛擬化整合,“大數據”與“云計算”相互生成,從而獲得了“云”的本源創造性。因此“云”不僅僅就是“云計算”和“大數據”,高視角地看,“云”是現代新文明的文化整合。
自然界的云是不確定性的形態,而“云”的本質就是不確定性,這種本質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整合,“云”也就是云文化。今天看來,不確定性是人類性的本質之一,“云”的內涵表現了這種超越的本質性。“云”以“云計算”和“大數據”等的相互分化和整合表現了知識和信息形態的再生,它的影響的深刻性和普遍性已不是隱含的了,比如人類最古老的觀念如時間、空間、歷史觀、世界觀、因果性、相關性、科學觀、法律,以至于自由、民主、共公性、個人隱私和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等等,都將受到深刻影響,“云”、“云計算”、“大數據”的出現標志一個時代的開始,人類以往的知識正在迎接一次刷新,所有知識性學科、社會學、經濟學、以及所有的社會科學各領域都面臨新的重構和重組,挑戰與機遇同在。
四、現代與未來之間的人——人性與人的文化
對于“人”來說,“云”最終聯于“端”,“云端”的移動化和各種涌現的終端硬件的智能化,不斷地使表象的人虛擬化,使“云”最終與“個人”這個最古老的概念聯接起來,人類再次直接面對人的個人性意義,個人空間的私有性本質以一種完全不同形式呈現在現代人面前,這是“人”的機遇,也是無可回避的挑戰。
對于工具理性而言,世界是開放的和平面化的,虛擬化技術使工具理性獲得了窺視個人所有空間隱私的能力,人怎樣保持個人的意義?“私有”的本質是什么?“云”如何實現現代人的個人本質?這是工具理性無能回答的關于自身本質的不可判定性難題,“云”在工具理性意義上的不確定性最終表現為人性的自由。
科學技術無國界,文明的傳播可以滲透國界的籬墻,但文化不能復制,文化的整合需要從個人心靈中自己生長,需要傳統與現代的變易。傳播科學技術知識,引進先進物質文明成果是歷史的自然和人自覺的文化整合過程,是不能人為政治化的,意識形態之墻的阻隔和照搬某個整體文明模式,同樣都是文明的極端。文化寓于傳統之中,割斷歷史,照搬某種“先進”意識形態去革命歷史、改造社會,只能走向末路窮途。“云”是現代社會的進程,文明可以拼嵌接軌,可以替代,網絡可以建設,“云計算”可以學習,“大數據”可以挖掘,但“云”的存在不能設計或仿造,圍墻之內不會有自由的云,創新能力是自性生長的,“學習”很難學習,沒有谷歌、百度也可,沒有臉書、博客可代,但這只是工具層次上的“接軌”,并不能替代自身的更新,個性和個人心靈的自由才是最強大的創造能力之源,人心是永遠自由的云,人的“云”才是智慧的淵藪,“人”不能被形式化,“人民”不等于“人”,否則,你就看不見他們,對“人”的拒絕或恐懼將在無形中扼殺最罕見的天才,窒息最偉大的創造,如果你沒有容忍異端的大國胸懷和氣質,你最多也就只是三四流國家,對“人”的拒絕最終會葬送時代的機遇,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文化也不等于就是形式上對傳統的繼承或文明傳播,文化不等于文明,文化不能以文明形式置換,文化更不能被工具化,“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烏托邦文明不是文化,封建政治制度也只是中國歷史文明的構成部份,無論繼承或拋棄,都不能直接當作中國傳統文化對待,拼接的歷史不是歷史,如果文化的整合本質被丟失,遺產商業化,儀禮“不欲觀”,勝跡成新偽,先進文明空殼化,人性虛偽化,這與文化的整合背道而馳,——在認知意義上,今天的“云”是最好的文化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改革教科書。
中國文化是本質人性的文化,與工具理性的根源性不同,所以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十字軍東征,也不會有產生宗教極端的基因,中國文化中缺少的是工具理性的土壤,中國長期封建歷史中就沒有制度私有制和相應的意識形態的根源,這正是資本主義沒能在中國歷史中自發產生的根本原因,中國近代歷史最根本的失誤就是沒有真正認識到對這種制度文明的引進的必要,這是封建主義亡靈至今不死的根本原因。中國文化歷史上不斷地實現了多民族的文化整合,因而延綿了數千年的歷史不絕。不幸的是,近代歷史以來,被西方強大的工具理性強奸了的中國封建文明愚蠢地打掉了腹中的孩子,中國文化的整合在最終完全失敗,迄今仍在這個泥淖中掙扎。歷史的中國己經錯過了工業文明的機遇,今天有幸地迎來了現代新文明的大潮,這是中西文化的互補性在變易中的實踐最好的機遇,但如果對此“買櫝還珠”,就會又一次錯過這個偉大的時代了!
轉載請注明出處:拓步ERP資訊網http://www.guhuozai8.cn/
本文標題:“云”——“大數據”的文化
本文網址:http://www.guhuozai8.cn/html/consultation/10839719602.html